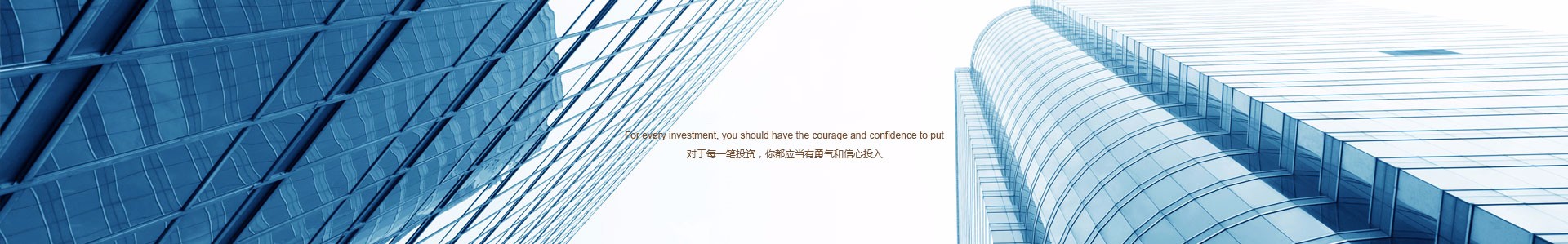百家乐- 百家乐官方网站- 在线Baccarat Online熊文聪︱游戏玩法规则:一个客观的实在
2025-11-11百家乐,百家乐平台,百家乐官方网站,百家乐在线游戏,百家乐网址,百家乐平台推荐,百家乐网址,百家乐试玩,百家乐的玩法,百家乐赔率,百家乐技巧,百家乐补牌,百家乐公式,百家乐打法,百家乐稳赢技巧,百家乐电子,百家乐游戏,21点,德州扑克,老虎机,快三,pk10,时时彩,北京赛车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作品,还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都是具象与抽象不可分离的双面体结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早就揭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任何符号都是由两部分构成,即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能指即感官化的“有声形象”,所指则是该有声形象在我们头脑中的抽象概念。[1]语言的本质既不在声音,也不在文字,而在差异。[2]说它具象,是说它是外在于人身的,借助文字、图形、色彩、声音等符号系统被人所感知;说它抽象,是说它不是单个的文字、图形或其他符号(因为这些符号很可能早就有了),而是符号之间所体现的位置结构、比例关系及组合对照(即基于选择所生发的“差异”),且这种“差异”是有内涵或所指的,是需要观者通过大脑的思考和演算才能够捕捉、解码和确定的。[3]不难理解,
《著作权法》第三条将作品界定为“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无疑是相当正确的。该立法表述(特别是其中的“能以”两字)充分揭示,作品不仅仅是那个外在的“表现形式”,更包含“能以”一定外在表现形式加以表现的、抽象的“思想内容”“比例关系”“位置结构”或“情节编排”,唯有如此,作品才真正称之为“智力”成果。《著作权法》第十五条对汇编作品的定义,非常精准、清晰地指明了什么是作品,即作品指的并不是被编排、被选择的若干片段、元素或内容,而是指“选择或编排”本身,只要该“选择或编排”体现独创性,那它就是作品。
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即在玩家操作游戏之前,游戏只是一堆静态的程序性代码,同时,一款游戏经每位玩家操作所呈现出来的视听画面是不一样的,这是否意味着玩家也参与了游戏的创作,并且只有在这个时候游戏作品才真正产生呢?其实,玩家会怎样操作游戏,经操作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动态视听效果,都是游戏开发者早就预设或限定好的,技巧好的玩家顶多只是在一个已有作品之上演绎出一个新作品而已。这就如同“一首歌曲,是词曲作者的智力成果,当它被歌唱家演唱时,便产生了一个新的演绎作品”是一个道理,无论是词曲作者的创作,还是歌唱家的演唱,都是作品,并且都是音乐作品。
还有人认为,《著作权法》第三条没有规定“游戏作品”,在游戏换皮语境下,换皮者往往不是直接抄袭、改编自原告游戏的源代码,故难以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予以规制。并且,游戏与类电作品、视听作品又有着天壤之别,无法类推适用,只能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管见认为,首先,暂且不论“反法”能不能提供保护(今年出台的新“反法司法解释”第一条便明确规定,只有属于违反著作权法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方可以适用反法第二条予以认定。言外之意,不违反著作权法规定的,则不适用反法),这种观点本身从逻辑上说就是前后矛盾的——不能予以著作权保护,不是著作权法力有不逮、提供不了保护,而是不应当予以保护,也即被告的行为是正当的,不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既然被告的行为是正当的,为什么换成反法又变成不正当了呢?
其次,根据外在表现形式之不同对作品进行分类,这不是可版权的前提条件,无论涉案作品分属于哪个类型,它都已然是作品了,就应当享有著作权。任何作品类型,无论外在表现形式如何,无论高低贵贱、也无论先来后到,都应当一律受到平等无歧视地保护,这不仅是贯彻《著作权法》第一条“鼓励创作”这一基本立法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严格遵守国际条约固有义务的必然要求——《伯尔尼公约》第二条明确规定,“文学艺术作品”一词包括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内的一切作品,不论其表现方式或形式如何。
再次,在《著作权法》修订之前,可以通过一定的解释方法(如把旧法第三条首句的“等”字解释为“等外等”;或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对作品的一般性定义解释为旧法第三条第(九)项的“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或从根本上否定旧法第三条是可版权性要件条款),来澄清误读、化解争论。《著作权法》修订之后,新的第三条不仅科学给出了作品的内涵,更彻底放开了作品的外延——开放外延不仅仅是说作品可以有无穷种类型从而囊括未来可能出现的崭新表现形式,更是在强调:只要它是作品,就无须再进一步分析或论证它是哪一类作品来评判其是否应当受著作权保护。[5]
最后,依此推理,作为智力成果的游戏(包含外在的视听画面和内在的玩法规则),只要满足作品的构成要件(具有独创性),就是作品,就应当受到著作权保护。无论是在旧法之下,还是在新法之中,都没有必要(而不是“能不能够”)再削足适履地将其视为或类推适用为类电作品、视听作品,即便游戏作品的确存在区别于类电作品、视听作品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对于评判它是否应当受到著作权保护毫无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列举作品类型是没有法律意义的,只是它的法律意义并不在于评判涉案智力成果是否应当享有著作权,而在于其他法律问题上——在界定权利内容、权利归属、权利限制和权利保护期等方面,作品类型之划分是非常有意义的。[6]
再一种观点认为,允许同一思想有不同表达,是为了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这种说法更是不着边际。著作权法从来都是鼓励而非禁止不同的表达(智力成果),如果创造“思想”概念只是为了说明法律允许有不同的表达(智力成果),那这就是一个多余的概念。并且,法律要做到只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即思想与表达在物理上是可分离的,但诚如前文所言,思想(抽象所指)与表达(具象能指)本身是任何作品的正反两面而已,它们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文如其人、文以载道,语言学家和社会大众做不到将二者分开,法官照样做不到。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思想/表达二分法”意义上的“思想”与“表达”,根本就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或语言符号学所理解的思想与表达,它们只是被法官巧妙地借来,用于降低其说服成本,提高其说服效果的修辞术而已。[7]它们同独创性概念一样,并不是为了解决实然层面的事实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应然层面的价值问题。说得再直白一点,著作权法真正不予保护的,不是抽象的但客观存在的思想,而是不具有独创性的、惯常化的智力成果,或非常伟大的、极其稀缺的智力成果。这是因为,假如这两类智力成果沦为私有财产,则会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大大抬高公众使用成本,所以应当将其排除在著作权保护之外。以下图表示即为:
结合游戏玩法规则而言,首先,不应当因为它是相对抽象的,便认为它是“思想/表达二分法”中的“思想”,从而排除在著作权保护之外。恰恰相反,游戏玩法规则通常是具有独创性的,它是游戏开发者的创作成果和智慧结晶,即便它是抽象的,但这种抽象与外在的、具象的连续画面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保护具有独创性的游戏作品,就必然要保护其中的玩法规则,否则就是否认游戏作品的存在。恰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太极熊猫诉花千骨”案中所明确指出的:“玩法规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是否受到保护,不应根据名称判断,而应根据具体表达方式,依照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规定特别是独创性的规定予以判断。”[8]当然,并非所有游戏(玩法规则)都具有独创性,它可能是很容易想到的惯常设计,在个案中将这种惯常设计认定为“思想/表达二分法”中的“思想”,无疑也是正确的。
其次,游戏玩法规则是否仅有技术功能或实用功能,而无审美功能或认知功能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符号编排体现什么功能,取决于该符号编排被使用的语境。当且仅当某符号编排与特定物质实体相结合,并在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解决生产生活实践的成本效益问题,我们才能说“实施”该符号编排是发挥了其技术功能或实用功能。相反,如果仅仅是在信息意义上复制、改编或传播该符号编排,而不是在物理意义上实施(制造、运用等)该符号编排,则只能发挥该符号编排的认知功能或审美功能。
最后,说白了,著作权法中的功能原则无非是对“思想/表达二分法”的重申和演绎而已,即当某智力成果已经成为该领域通用的、人人都绕不过去的(或者说绕过去的成本极高)、非常有限的乃至于唯一的智力成果时,我们就说该智力成果具有(实用)功能,不应当再作为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在具体个案中,不排除说某个游戏玩法规则已经成为该领域内通用的、绕不过去的、非常有限的乃至唯一的思想之表达,此时的确应当将其排除在著作权保护之外,但前提是应当由被告举证证明。
所谓游戏换皮,是一种形象化的通俗说法,指的是通过替换原告享有著作权保护的游戏作品之连续画面、美术设计、角色形象、文字语句、音响音效等外在的视听表达,但仍然沿用其地图布局、玩法规则等内在的编排设计之手段。说白了,未经许可的换皮仅仅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具有一定隐蔽性的抄袭而已。实际上,换皮并非游戏产业所专有,将由一国语言文字写就的小说翻译成另一国语言文字,其实也是在换皮,因为它也是替换了原小说外在的文字符号这层皮肤,甚至还改动了原小说中句子、段落等语法结构,但未经许可的翻译显然是构成侵权的,因为它再怎么翻译、再怎么换皮,都是换汤不换药,都是复制、使用了原小说的内核——语言符号的编排选择、思想内容,也即作品的所指。此时,我们能主张因为小说的情节、内容或结构不是文字作品,所以不受保护吗?
实践中,诸多裁决也表明法官的观察和判断是正确的。如在“守望先锋诉英雄枪战”案中,法院认为:“被控侵权游戏与《守望先锋》在五张游戏地图的游戏玩法、行进路线、该地图相对位置建筑物的排列、进出口的位置选择、该地图的取胜条件、血包点的存放位置、绝大部分英雄的类型、技能和武器描述、武器释放效果等方面均存在大量的相似,可以认定构成实质性相似。”[10]在“太极熊猫诉花千骨”案中,法院指明:“认定在后游戏是否实质利用了在先游戏玩法规则的整体表达,应就玩法规则体系进行整体比对,先判断单个玩法系统的特定呈现方式上是否构成相同或实质近似,再看整体游戏架构中对于单个玩法系统的整体选择、安排、组合是否实质相似。整体判断时不仅应当考虑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单个玩法系统的数量,还应考虑不同玩法系统对于游戏玩赏体验影响程度以及是否属于游戏设计重点、游戏盈利点等因素以综合判断。”[11]
另一方面,作品的能指与所指也不是固定不变地捆绑在一起,某一所指可以对应不同能指;某一能指也可以对应不同所指。在所指相同的情况下,即便能指差异较大,也可以认定这两个作品相同或构成实质性相似。也因此,在进行侵权比对时,需要法官认识到作品的整体与局部、表面与内在是辩证统一的,透过看上去不相同甚至不相似的外在视听表达,去探问其内在所指是不是相同或高度重合;透过单独比较作品的组成元素去把握两个作品是否在整体上构成实质性相似。
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著作权法中的“实质性相似”并非单纯的事实认定,而是复杂的价值考量,故在进行侵权比对时,法官不应仅仅局限于两个作品听觉或视觉上的比较,也要分析二者相对抽象的所指(如结构框架、情节内容、玩法规则等)之相似程度;更应结合被挪用部分是否构成原告作品的核心关键;被控侵权方为这种改动或换皮投入了多少体力、脑力和财力;从相关公众的理解和认知来看,被告作品是否构成原告作品实质性替代;被告的作品类型是否为原告通常会开发的衍生品市场;以及被告挪用、模仿的主观意图等因素或原则进行综合的评判,从而在遏制抄袭与鼓励创作之间保持应有的平衡。
综上所述,游戏的核心组成就是玩法规则,玩法规则虽然相对抽象,但却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一种智力成果,游戏(玩法规则与视听画面的有机整体)只要具有独创性,就是作品,就应当享有著作权保护。在评判涉案游戏(玩法规则)是否应当受到著作权保护时,没有必要再进一步探究它是不是类电作品或视听作品,能不能将其视为或类推适用于类电作品或视听作品。玩法规则由动态的连续画面来呈现和贯彻,游戏画面之所以是连续的、有逻辑的、充满情趣的、富有吸引力的,就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内核与灵魂——玩法规则。尊重客观事实,尊重他人的智力创作成果,尊重产业的技术研发与物质投入,打击不诚信的抄袭和搭便车行为,这是最基本的法治要求。